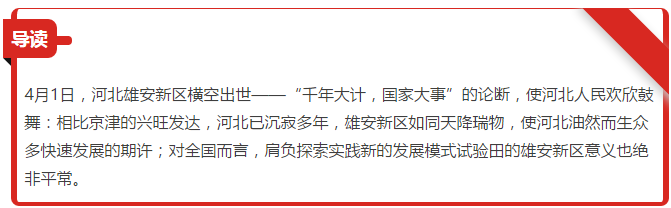

雄安新區的設立也引起了國外輿論的廣泛關注。河北雄安新區設立對河北、全國產生哪些積極意義和引領作用?河北雄安新區規劃建設最大的挑戰和瓶頸是什么?如何破解挑戰和瓶頸?如何實現實現“世界眼光、國際標準”的規劃建設理念?為此,本刊獨家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
新區的設立和建設意義與現實作用都很巨大
“河北雄安新區的設立、建設,正如中共中央、國務院所說的那樣,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它不僅具有宏觀指導、引領的巨大意義,同時,在實實在在的踐行城市可持續發展、經濟綠色低碳發展方面同樣具有巨大作用。”潘家華認為,河北雄安新區的設立和建設具有如下6方面意義和作用。
其一,全國示范意義。我國的資源配置一般是與行政級別聯系比較多的,這就造成國家的優質資源多集中在首都、一線城市和各省會城市,這些城市也因此患上了交通擁堵、環境污染、人口過度密集、資源環境承載力日趨減弱的大城市病。其他城市的資源諸如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等優質資源都比較欠缺,發展后勁不足。如果雄安新區能夠將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的優質資源進行疏解,進而形成區域均衡發展,那么北京城市病將得到緩解甚至根治。北京城市病得到緩解也會對全國其它一線城市、省會城市的城市病治理起到示范作用,促進這些城市將其非核心功能的優質資源轉移到其它發展水平低、技術落后、資金短缺、人才匱乏的中小城市,使大城市病得到緩解、根治,使發展滯后的中小城市得到發展的資源和機會。
其二,使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能真正落到實處。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問題提出最少三年了,但收效甚微——盡管北京人口近一步膨脹速度在減緩,但總體上人口總量仍在增長,這說明之前的疏解沒有取得突破性成效。其原因在于,北京和周邊地區的勢能差距太大,北京是高大上,周邊是低矮矬。正所謂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北京眾多優質的教育資源、醫療資源和眾多的就業機會對周邊各種資源產生巨大的虹吸作用,這是其它城市無法比擬的。雄安新區的建設高起點、高規格,“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給人們帶來很高的預期:優質的教育資源、文化資源、醫療資源、就業環境可與北京媲美甚至比之還好。這樣的話人流、物流、資金流容易向雄安新區流動,雄安新區成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北京和雄安人文水平類同,優質資源旗鼓相當,而且京津雄幾乎同城化,現代軌道交通鏈接壓縮空間距離感。雄安獨樹一幟,甚至更有吸引力,疏解阻力也就自然而然的化解了。
其三,實現北京、雄安新區雙重綠色低碳發展。原來的京津保腹地的雄縣、容城縣、安新縣因分散難以統一規劃,如今以雄安新區之名統于一體,實現了集中。高起點、高規格的規劃,一張藍圖干到底,保證了雄安新區在綠色、低碳的軌道上發展。北京也將因非首都功能的疏解而更加綠色低碳。
其四,對華北尤其對河北引領示范效果顯著。京津冀協同發展難點在冀。一直在說,要河北承接,可河北究竟有多少承接的能力呢?它承接的抓手在哪里?在雄安新區設立之前這都是要回答的問題。現在雄安新區成為問題的最佳答案,這個集中承接載體集京津冀乃至全國之力、高起點、高規格設立、建設的新區使包括河北在內的華北地區看到了希望,使河北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有了實實在在的載體和抓手,有了標本和參照,對河北發展起到明顯的引領示范效應。雄安新區設立后僅一個月時間,石家莊市就宣布即將把四大班子機關整體遷入正定新區,表明石家莊作為資源集中多元的省會城市之疏解,不是“高歌不進”,而是擼袖實干。
其五,與長三角、珠三角形成多中心協同、多功能互補城市群發展引領、示范。在京津冀,北京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現有的如教育、金融等其他非首都功能將轉移到雄安,天津則是華北經濟中心,這樣在京津冀就形成多中心協調、多功能互補、互為強化的城市集群優勢。這將與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一道引領、示范中國城市發展。
其六,樹立高起點、高規格審慎建設的標本。雄安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要從長計議。在這樣的定位下,雄安新區必須是綠色、低碳、節能、宜居的,必然與自然相協調、相融合,絕不允許以破壞環境生態為代價謀取短期不可持續的發展。分期建設也正說明了這點:近期建設100平方公里,中期200平方公里,遠期2000平方公里。這表明,雄安新區的建設秉持的是審慎符合客觀規律的原則,不是沿襲攤大餅式建設,不是一步到位。雄安新區建設走的是在高規格、高品質實踐的同時,摸索經驗以確保新區沿著綠色、低碳、宜居的維度發展。
新區的規劃和建設要以水環境容量為依據
在潘家華看來,河北雄安新區存在的生態環境問題中,最成問題的問題也是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雄安新區所在地水環境容量偏小的問題——盡管新區所在地擁有華北地區最大的淡水水域白洋淀。
正確認知雄安新區的環境問題
記者:盡管雄安新區的選址已經充分考慮環境容量問題,但實際上,新區所在地在環境方面仍存在不少問題。應如何看待這些環境問題?
潘家華:京津冀地區屬于產業偏重地區,尤其是河北省。在河北省,保定、石家莊等地空氣污染問題很嚴重,但我個人認為,位于京津保腹地的雄安新區的大氣污染問題比水環境問題要好解決得多:大氣污染問題通過使用清潔能源、節能和調整產業結構,能夠得到緩解,直至被徹底解決,而水的問題相比而言更難解決。因為現在雄安新區人口密度還比較低,污染排放量也不是那么大;雄安新區將來不會是以原材料生產、高耗能、高排放為主的制造業集中地,所以,雄安新區不會成為大氣污染物集中排放地。當然,工業污染少,并不意味著生產生活產生的污染可以避免,因為人都要食人間煙火,有人間煙火就有排放。雄安新區環境問題的核心是水環境的容量問題。雄安新區所在的華北地區屬于半濕潤半干旱地區,年均降水量只有492.3毫米,只是略高于劃分中國西北半干旱與東南半濕潤地區的人口密度“胡煥庸線(“璦琿—騰沖線)”的400毫米降水等值線,比北京的644毫米低近1/4。從氣候變化的角度分析,雄安新區年平均降水量正以每十年5毫米至20毫米的趨勢減少。據1961年至2016年的監測數據,雄安新區年平均氣溫正以每十年0.1℃至0.3℃的幅度升高。降水不多,而且減少趨勢明顯;升溫持續,蒸發量則呈增加趨勢。地表徑流本來就比較少;雄安新區中的雄縣、安新縣、容城縣是農業大縣,多年來,為了保證對農作物的灌溉,使地下水過量開采,造成華北地區地下漏斗形成;由于當地農業及工業的水消耗,造成本來就少的地表徑流被截斷,進而使地下水的補充水源減少甚至消失,致使華北地區最大的潛水型淡水湖白洋淀經常面臨干涸的困境。
記者:剛才您提到雄安新區生活污染排放的問題,那么如何盡量減少生活污染排放?
潘家華:雄安新區三縣現有人口大概130萬,按照100~200平方公里、城區人口每平方公里1萬人計,新區人口凈增100~200萬。人口集中必然意味著用能、耗物、用水的高強度,根據物質不滅定律,必然廢氣、垃圾、污水集中高密度排放。消耗排放不可能歸零,但是可以減量循環。首先,生活用能要盡量清潔化,消除直接燃煤,代之以電、氣、可再生能源。交通應以電動汽車、非機動車為主,盡量少用汽油車、柴油車;建筑內的生活、辦公用能盡量多用太陽能,雄安新區所在的保定地區太陽能是比較豐富的,應盡可能利用。其次,生活固廢的處置,要杜絕垃圾圍城。按人均1公斤垃圾計,每天生活固廢可望達2000噸甚至更多。廚余垃圾可生物降解制肥還田,其他固廢除可回收的外,只能焚燒,因為雄安沒有地方可以填埋垃圾。而且即使少量填埋,地下水污染,遺患無窮。生活用水按人均每天偏低的100公斤計,每天不低于20萬噸生活污水。白洋淀湖區水質功能應該在III-IV類,而實際上為IV-劣V類,是較為嚴重的污染水域,不具備污水自然凈化功能。生活用水涉及生活品質,減量有限;最有效的是中水回用,減少排放。中水回用多為園林綠化和農業,這就要求污水中杜絕重金屬、消除有毒有害化學物。
主輔并用解決新區水環境容量偏小問題
記者:如何破解雄安新區水環境容量偏小的難題?
潘家華:策略有主有輔。在盡量擴充雄安新區水環境容量這個問題上必須主輔并用。主策略有三。第一,從規劃開始就確定以水定產能、定產業結構、定人口。雄安新區在規劃之初,在建設、管理過程中,一定要以水環境容量為基礎。這方面北京已經這樣做了。雄安新區必須以水定人、以水定產,使新區產業結構和用水需求相適應、相吻合。
第二,大力發展現代化節水農業。雄安新區所在的地區,農業用水量很大但效率低,需要提高灌溉技術、調整農業產業結構,釋放一部分用水量,以滿足其它產業用水。這方面可以向以色列學習。以色列人口更為密集,比京津冀地區降水更少、水資源更缺乏,但其農業卻很發達。為了破解惡劣的生態環境對農業的桎梏,以色列在節水技術、設備等方面進行技術攻關,使節水技術、設備位于世界前列,因而保障了在惡劣環境下農業的高水平發展。有人會問,既然在雄安新區農業是用水大頭,能不能取消當地的農業呢?我認為不能。雄安新區所在的三個縣,農業規模大、基礎比較好、勞動力比較多,取消農業不現實、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只要以以色列農業發展模式為方向,大力提高節水技術、采用高效節水設備,向著現代化節水型農業方向發展,農業用水一定會被釋放出來一部分。
第三,通過南水北調區域間調水。南水北調涉及京津冀,調水量已分配完畢,河北的配額中包括保定,但不包括雄安新區,因為配額早已分配完成,而雄安新區才剛剛宣布成立。現在面對雄安新區有限的水環境容量有必要對南水北調中京津冀配額進行重新分配。比如拿出京津冀總配額的十分之一,這對原分配方案影響不大,較容易實施。這部分看似比例不大調劑過來的水,對雄安新區來說是重要來源之一。
此外,我們需要注意,農業生產是季節性的,城市用水是不分季節不分晝夜的。而華北地區降水季節性很強。這就意味著,在降水集中的夏季,需要儲水、補充地下水。雄安尤其不可學北京,將圓明園、園博園的水域通過敷設防滲布蓄水保水,斷絕地下水源補給。面子工程不可取,地下水漏斗要補平。
記者:為了擴大雄安新區水環境容量,有關人士提出將海水淡化后引入雄安新區,您怎么看這一方法?
潘家華:海水淡化后引入雄安,我覺得這個方案不可取、沒必要。如果換一種思路的話,應該可行:雄安出資,河北、天津沿海的地方搞海水淡化,并使用淡化后的海水;與此同時,把與雄安出資淡化水的額度等同的南水北調分配給天津、河北的南水配額調劑給雄安新區。
記者:除了您說的以水定產能定產業結構定人口、大力發展現代化節水農業、區域間調水、海水淡化置換南水的方法外,還有沒有其它方法?
潘家華:有,但除上述之外都是輔助性措施,如中水回用、水循環利用、節水措施等等。在這里有必要強調一點,生活方面的節水不能為節水而節水,不能以犧牲生活品質為代價節水。在現實生活中,有些地方把廁所搞成水流很小、甚至免沖;有的地方賓館淋浴出水量非常小,這些措施往往省了水,卻犧牲了生活品質。如果既省水又不降低生活品質那肯定沒問題。中水回用、水循環利用要以用水保障、安全為前提,沒有用水保障、沒有安全前提不行。
不能以犧牲其它地方環境為代價
記者:水容量偏小是雄安新區最大的環境問題,在解決這個問題過程中,應該站在怎樣的高度考慮解決問題?
潘家華:雄安新區規劃、建設必須放在全國一盤棋的高度考慮。必須認識到,水是雄安新區發展最嚴峻的挑戰、根本的瓶頸,所以必須以水的滿足量為新區規劃建設的前提,把水的滿足量作為產業結構、產業布局、人口數量的依據。雄安新區是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但不是唯一承載地;雄安新區也不是要承接所有北京非首都功能。像高耗能、高耗水的項目可以放在其它可以承接、能源和水源比較充沛的地方。雄安新區的發展真的沒有必要以犧牲其它地方的生態環境為代價,以其它地方的生態環境容量來擴充自己的環境容量。如果非要這樣的話,那雄安新區的意義就要大打折扣了。
規劃建設中的“世界眼光,國際標準”
“世界眼光,國際標準”是雄安新區規劃建設要求的一部分。能否達到這樣的要求,將決定雄安新區能否承擔“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的重任。
我國城市規劃已經是世界眼光了
記者:如何實現“世界眼光”設計理念?
潘家華:如今的中國已經站在世界中心的層面了,中國的眼光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經是世界眼光了。我們要有這樣的自信。中央講要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雄安新區的設立、建設就是這種自信的體現。我們現在所從事的城市規劃,顯然比發達國家在工業革命初期、中期的規劃建設要科學的多、完美的多、低碳的多。而且,我們現在的規劃既吸取了發達國家的教訓也吸收了他們的經驗,同時加上了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經驗,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世界的眼光,是真實存在的,甚至可以說我們的眼光就是世界的眼光。同時,我們有責任、有義務引領世界城市化發展的進程。當然,雄安的世界眼光,還要廣泛吸取世界都市規劃、建設、管理的先進理念和經驗,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美國的華盛頓特區(只有國家政治中心的功能)、巴西的巴西利亞(遷都、區域協調平衡)、西德的波恩(臨時首都的政治中心,不搞多功能的現代城市建設)、日本東京圈的疏解、印度的“新”德里(保留德里,建新區)、荷蘭的名義首都(阿姆斯特丹)實際政治中心(海牙)不重疊、南非的多政治中心(行政首都(中央政府所在地)為茨瓦內,立法首都(議會所在地)為開普敦,司法首都(最高法院所在地)為布隆方丹),應該都可以借鑒。
雄安新區規劃建設要以扁平化為理念
記者:如何實現“國際標準”?
潘家華:必須要在扁平化的理念指導下規劃建設雄安新區。扁平化強調宜居、便捷,與自然和諧相處,這也是黨中央國務院規劃建設雄安新區的要求。扁平化講的是城市里職住一體、產城一體,多中心協同、多功能融合——不能建成像北京天通苑、回龍觀那樣功能單一的睡城,也不能建成北京亦莊那樣只搞工業不做其它。天通苑、亦莊不是扁平化是極化。
記者:發達國家有哪些是單中心國家?
潘家華:發達國家有單中心的例子。英國只有一個中心倫敦,法國只有一個中心巴黎,挪威只有一個中心奧斯陸。為什么這些國家只有一個中心呢?那是因為工業文明的特點所要求的:工業文明必須講集中、講效益,集中才有更高的效益。這樣的單中心忽略了與自然的和諧,沒有顧及人類是否宜居。
記者:發達國家中有沒有扁平化多中心的例子?
潘家華:發達國家中也不乏扁平化發展的例子。美國就是比較好的扁平化:紐約是世界金融中心,由于聯合國總部駐地的原因成為世界政治中心,但并沒有成為美國的政治中心,也沒有成為教育中心,州立大學沒建在那里。再如,美國加州大學有10個校區分布在加州南北各地,沒集中在一起。歐洲的荷蘭也是扁平化。荷蘭名義行政首都是阿姆斯特丹,實際行政首都是海牙,經濟中心城市是鹿特丹,烏特勒支是教育、產業中心,它是一種典型的扁平化的多中心各種功能互相協同、互為補充。雄安新區的規劃建設應該是以扁平化理論作為指導建設的多中心、職住一體、產城一體、多功能融合的宜居、低碳、綠色城市新區。扁平化的設計可以解決早進城、晚出城的潮汐流問題,從而根本解決城市交通擁堵的問題。由于職住一體,可實現就近就業,上班步行就可以從容實現了,不需要化石能源乃至于機械驅動的交通了。例如,一座城市有如一個大學校區,例如英國劍橋,生活工作就醫就學近便,無需工業文明意義上的交通了。這樣的話,城市能耗降低了,大城市病也不會出現。
來源:節能與環保雜志

 上一條
上一條

